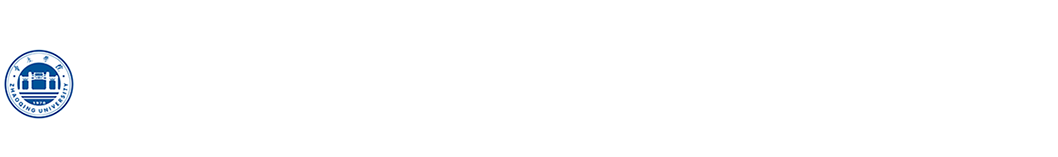人文主义也被译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它与博爱主义(humanitarianism,亦译人道主义)有相通之处。人文主义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箴言——
“人是万物的尺度”。作为对所向往的人性的追求,它在文艺复兴时期扬弃了狭隘的哲学体系、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把价值由以神为本转变成以人为本,鼓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致成为一种普世文化;在20世纪,它形成了以肯定人的根本价值、强调人的尊严为主旨的思想运动。现在,人文主义泛指关于人的本质、意义、使命、地位、价值、特性等的理论和学说,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人文主义的思想菁华和终极意义在于以人为本,以纯真的爱和天赋的善追求人类的最大福祉。
科学主义 往往被不确切地译为“唯科学主义” 是伴随着近代科学 本文“科学”一词主要指“自然科学” 的诞生和成功逐渐形成的。它指称科学家的或归之于科学家的典型的方法和态度,例如 科学是对真知的追求,是对自然 乃至社会 规律的揭示;科学知识是最为客观的、最接近实在的知识;科学的统一在于它的方法而非材料,科学的实证、理性、臻美等方法可供其他学科借鉴;科学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必须以技术为中介 ,是推动文明进步和造福人类的源泉之一。科学主义在18世纪的机械物质论、19世纪的孔德实证哲学和社会物理学、20世纪初叶的逻辑经验论中被推向极端,以至夸大科学方法的功效,无条件地把它应用于所有学科 科学方法万能论 ,乃至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 科学万能论 。这种激进的科学主义失之偏颇,受到人们的批判和贬斥,现今在科学共同体内已经没有多少市场。
在古代和中世纪,人文 学科 和科学 萌芽状态的 本来就是并蒂莲,在文艺复兴时期昌盛的人文主义反对蒙昧主义,崇尚理性和智慧,主张探索自然、研究科学、追求知识,从而成为近代科学的助产士;而科学的问世和蓬勃发展也为人文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和物质资源。18世纪以来,经典科学的羽翼日益丰满,科学主义随之相伴而生。科学主义固然有助于提高科学的威望,促进科学的建制化,但是它的过分张扬和强势“中轴”地位,客观上对人文主义构成某种挤压。加之人文主义既未摆脱先天的贵族式的夜郎自大,又盲目沉溺于对科学的无知,从而导致两种文化分道扬镳,造成人类文化发展的失衡。
人文主义偏重人、主体、人生、主观、个体存在、自由意志、价值、直觉、体验、情感等,与之正好相对,科学主义则侧重物、客体、自然、客观、普遍规律、因果决定、知识、逻辑、实证、理性等。二者关注焦点的差异既显示出各自的长处和优势,也是其不足和缺憾之所在。诚如J.S.赫胥黎爵士所言 “科学的心理的害处是理智主义和缺乏对于它种经验的价值的鉴识和推重,过度着重行动而轻视存在和感觉。人文主义心理容易陷入的害处是轻视那种慢而无误的归纳和实验方法,对于自然的事实和法则默然无知,不一步一步地工作而相信从幻想的捷径可以达到成功。”
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主义是蹩足的和虚浮的。因此,急需改变两种文化分裂的态势,急需消除两种主义的人为对立。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既不是削足适履、刓方为圆,也不是揠苗助长、一蹴而就,而是使二者在相互借鉴、彼此补苴的基础上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两种文化汇流和整合的有效途径是,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scientifichumanism)和人文的科学主义(humanistscientism),即走向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和新科学主义(neo-scientism)。
科学的人文主义是在保持和光大人文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给其注入旧人文主义所匮乏的科学要素和科学精神。它的新颖之处在于 树立科学的宇宙观或世界图像,明白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一;尊重自然规律和科学法则,对激进的唯意志论和极端的浪漫主义适当加以节制;科学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自身也能够提供新的价值和意义,依靠科学自身的精神力量和科学衍生的物质力量,有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科学的实证、理性、臻美精神以及基于其上的启蒙自由、怀疑批判、继承创新、平权公正、自主公有、兼融宽容、谦逊进取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思想、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方式是我们思考和处理社会和人事问题的背景和帮手,科学人的求实作风和严谨风格值得人文人学习和效仿;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要尽可能学习和借鉴科学方法,以拓宽视野,更新工具。要而言之,科学的本性包含着人性,科学的价值即人的价值,科学的人文主义就是人文主义的科学化。
同样,人文的科学主义是在发掘和弘扬科学主义的宝贵遗产的前提下,给其增添旧科学主义所不足的仁爱情怀和人文精神。它的鲜明特色是 人为的科学理应是而且必须是为人的,为的是人的最高的和长远的福祉,它因此必须听命道德的律令,这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科学只提供手段,而不创造目的,对价值判断先天乏力,它应该尊重并辅佐人文主义的导向作用;科学的误用或恶用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科学人应该念念不忘科学良心,时时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制止科学的异化和技术的滥用;纯粹的智力难以弥补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失,科学人切勿以救世主自居,要虚心向富有人文精神的贤人和哲人学习,从人文学科中吸取各种营养;适度冲淡科学的“冷峻”面孔,扶助科学中本来就有的为善、审美功能,让情感成为科学活动和科学发明的积极因素。总之,人性应该寓居于科学之中,人的智慧亦是科学的智慧,人文的科学主义就是科学主义的人性化。
关于科学的人文主义,生物学家J.S.赫胥黎和科学史家G.萨顿都曾做过精湛的论述,但是人文的科学主义好像是新提法。不过,它们在历代的哲人科学家身上得以双重体现。例如,20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20世纪科学革命的主将和哲学大师爱因斯坦,都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的人文主义者和人文的科学主义者。只是在20世纪后半期,这样的哲人科学家显得相对少了一些。另一方面,类似哲人科学家那样的一身二任式的科学的人文家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比如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歌德,但是这样的伟大人物后来似乎销声匿迹了。究其原因,在于知识门类的极度分化,在于教育的专门化和文理分家,致使科学和人文的学子和学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最终酿成二者之间的巨大鸿沟。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状况现在正在向汇流和整合的方向转化。首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出现了相互渗透、相互融会的趋势,已经产生了一批交叉科学或边缘学科。其次,我们已经成功地编织成联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纽带,建造起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比如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者有中国特点的自然辩证法。再次,在作为人类知识总汇的哲学内部,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流派也呈露出相互取长补短的会通态势,催生出所谓的文化哲学。最后,现今人们已经认识到通才教育文理齐头并进,知识教学与素质教育并重,理论与实践经验密切结合,既是智力的训练也是人性的修养,这为未来的哲人科学家和科学的人文家的涌现创造了前提条件。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两种文化的汇流和整合就不是遥遥无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