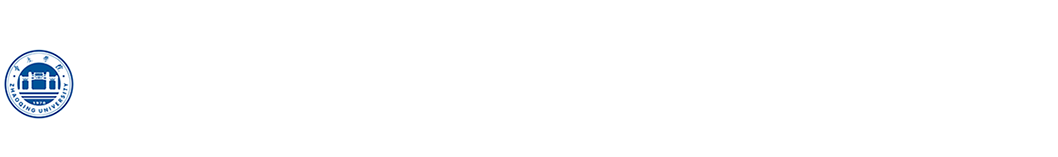古老中华素以礼仪之邦著称。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相信“天命”,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天决定的。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则被称之为“天子”,“天子”被认为是“天”的代言人及其意志的执行者,因而人们对“天子”总是怀着崇敬和畏惧的心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政治生活中,君主的言行好恶无疑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平民百姓的好恶产生直接影响。而正是专制君主及其统治阶级的这种导向作用,造就了不同朝代文化的不同特色和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与学术文化的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时代,“天子下降,诸侯上升,大夫执政”,体现了当时政治变化的特点。春秋伊始,周室丧失了对诸侯国的约束能力,诸侯国内部以及诸侯国之间的篡杀、攻伐层出不穷,空前激化。各国对内要求社会安定、富国强兵,对外要求生存、争霸权,面对这种局面,各国统治者以及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寻求治国安邦之道。这就为百家蜂起奠定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正是随着政治、经济方面激烈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学术文化领域出现了各种学派,不同的思想在交锋中相激相荡。《汉书·艺文志》说:“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行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各国的学术政策都十分宽容,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因而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诸子百家应运而生,百家争鸣的局面终于得以形成。但不论是主张“仁政”的儒家,还是主张“兼爱”的墨家,主张“无为”的道家,或是主张“法治”的法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以自己的见解为标准来衡量别人的见解,以自己的主张去游说各国统治者。可以说,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导向的这种多元化,导致了这一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这就表明,百家争鸣的实质是当时多元政治导向的必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还与“士”阶层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末年,官学衰微,私学兴起,逐步产生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即所谓“士”阶层。孔子就有弟子三千,这个数字不为小。到战国时代,“士”阶层越发庞大,各国统治者对这些人也另眼相看,纷纷罗致,导致“养士”之风盛行一时。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秦国文信侯吕不韦等人的门下食客动辄几千人。因为这些“士”有文化,有思想,统治者对他们就不得不重视,于是经常让他们在内政外交上献计献策。而这些“士”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有的甚至可以通过一席话获得很荣显的地位,所谓“朝为布衣,夕为卿相”,故也乐于游说各国,或者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商鞅、张仪等人都是因入秦游说而被拜相的,稷下学宫士子云集,也是很好的说明。而这种社会现状无疑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提供了人才基础和思想基础。
唐代皇帝的爱好与唐诗的兴盛
一般都认为盛唐是东方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它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又一个光彩夺目的高峰,而唐诗无疑是这座文化高峰上的璀璨明珠。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华,蜚声四海,映照古今,其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艺术之精湛,都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若追溯唐诗的起源,应该说是魏晋以来文风不断转变发展的结果,但唐诗的繁荣又确实得益于唐代统治者的“导向”作用。唐朝的皇帝,特别是前期的皇帝几乎都擅长诗赋,多有作品传世。作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不但在政治上具备雄才大略,同时也是一位写诗高手。虽然他的诗宫廷味较浓,但他的示范作用影响了他周围的文人学士,并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唐玄宗的祖母武则天与伯父唐中宗也都是诗人,他们倡导宴饮赋诗,群臣应制,有时一次多至百篇,那些不擅长作应制诗的大臣,便很难参与朝会。到盛唐时期即玄宗、肃宗时期,也是唐诗最繁荣的时期,诗坛人才辈出,群星璀璨,风格各异,流派纷呈。高适、王昌龄的边塞诗,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更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终将唐诗推向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
唐诗的繁荣,除皇帝爱好的原因外,也得益于诗歌在士子入仕中的导向作用。唐以进士科取士,应试者必须长于作诗,而这也就成为士人们获取功名的正路,唐诗也因以诗赋取士而繁盛起来。高宗时,进士科加试“杂文”(诗赋),是以诗文茂美者入选之始。及至盛唐,诗赋取士更见推重,玄宗朝的进士及第或位极卿相者如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是精于诗赋的。唐朝的文官几乎无一不是诗人,诗作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清康熙时曹寅辑的《全唐诗》,所收诗达48900多首、作者达2300多人。应该说,这一数字虽然惊人,但仍然不是全部。
朝廷看重诗人,世人仰慕诗人,诗人在盛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在这种社会导向下,许多文人学子都把追求诗“境”作为自己的理想,诵习诗赋也成了士子入仕的敲门砖。李白刚到长安时,因没有什么名气,便带着自己的诗作去晋谒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看了他的《蜀道难》,扬眉赞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他把李白推荐给玄宗,李白得以“供奉翰林”,从此名扬天下。那些慕名者也接踵而至,以得李白品题为进士中举之捷径。有个叫魏万的人,从河南跟踪李白,奔波三千里,终于得到李白的《还山诗》一首,魏万靠此诗居然金榜题名。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社会的导向作用对唐诗的发展与繁荣有着何等的影响。
宋代的文人政治与宋词的极致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其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场,在许多城市也都有歌楼伎馆,甚至有些官僚豪绅家里也有歌伎舞女,这种社会风尚为宋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宋词数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编的《全宋词》,含著名词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科举取士与古代士人的追求
创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到明清达到极盛。科举考试破除了以门第高下作为选官取士标准的腐朽制度,打破了由豪门士族把持国家政权的政治格局,为庶族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入仕从政的道路。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系起来,使广大读书人“头悬梁,锥刺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朝着统治者规定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方向努力,憧憬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举成名天下扬”的美好明天。
科举制度对士人的这种导向作用在明清时期达到极致。明清两代,在沿袭往代科举旧制的基础上,经过增益补充,体制更加完备,规模更加扩大,程序更加固定化,文体更加程式化,考试更加复杂化,而且500多年间没什么变化。明清两代共开科201次,考取进士43000多人。可见,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对全社会的“读书热”有何等影响。明末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惊叹中国简直是个“文凭社会”。由于科举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考中与否直接影响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所以,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参加科举考试就是为了考中而升官发财。士人信奉的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科举制度也就把士人引进一条死胡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许多读书人甚至文盲都会背诵这样一首流行一时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据传,北宋时期的梁颢,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开始科考,一直考了47年,直到北宋太宗雍熙二年终于喜登龙门,于82岁时中了状元。他在《谢恩诗》中写道:“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载始成名。”这诗中有及第的喜悦,但于喜悦中也透出令人心酸的悲凉。而这也正是当时许多士子的真实写照。
从以上四个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繁荣中的“导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各个时代因其“导向”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文化形式,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