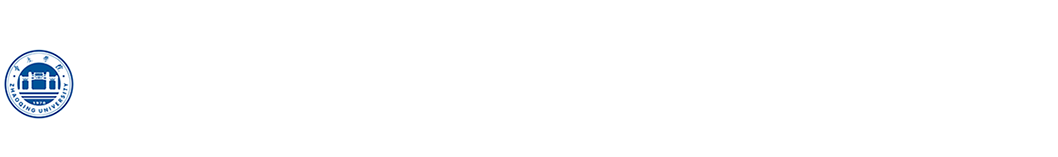作者:黄振萍(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